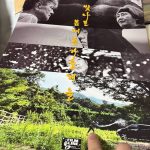每到任何一個城市,我一定會探訪當地最大或者最有意思的書店。
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人民可以毫無障礙地交流,雖然我對兩國的語文完全沒有概念,卻很留戀布拉格和布拉提斯拉瓦這兩個首都的小書店。站在書叢間翻動當地的文學作品,瀏覽冊葉間的設計,嘗試咀嚼拉丁字母鋪砌成的陌生語句,摸索不懂內容也居然可以花掉一兩個小時。
我走過中國大概四十多個城市,去過無數的大小書店。在首爾,我最喜歡逛的地方也是書店。工作忙碌起來,一個禮拜內幾乎沒有準點下班的時候。
而公司附近就有首爾數一數二的教保文庫和永豐文庫,要是遇到壓力龐大,需要調解思緒的話,哪怕只是趁打烊前逗留片刻,我也偶爾會過去瞎溜,聞一下書卷味。
不知道是因為寂寞,還是因為供應太充足,我時常會有想要買書的衝動。加上這是一個幾乎每個人都在趕時間,似乎每個人都很努力在生活的城市,我特別害怕自己懂的東西比別人少。
有時候買了,不一定會從頭到尾讀完整本書,充其量不過是填補自己對學問的焦慮。書本,總是給我踏實的安全感。
我們家在五、六十年代非常貧窮,伯父小學沒畢業,把機會都讓給了父親,但我很肯定自己不曾在父親身上承嗣任何對書籍的眷戀。伯父在一個經濟開始騰飛的時代長大,或許由於學歷低,當時的他和現在的我有著同樣對知識的惶窘和不安。從明清的經典到金庸的武俠,從馬來的傳記到英美的科普,我一直記得家裡那個裝載了求知慾的書櫥。
「要一個人愛看書,就先讓他喜歡上書。」
伯父的這句話,對我造成畢生的影響。我對書本最初的記憶,從他不過濾內容買來的《老夫子》開始。要是連畫冊都不看的人,肯定不會花時間在字斟句酌的作品上,這是當時的他和現在的我都心折首肯的想法。
但是愛書卻又未必具備世界觀。
我身邊不少一心鍾愛華文書,但恐懼英文、抗拒馬來文的人。在這些朋友眼中,誠品是華文世界的文化圖騰,每到臺北必朝聖。我也同樣迷戀誠品的格局和氣度,而且永遠不會空手離開。
但是,我對多元的語言世界有渴求,我無法讓自己停留在文字單一的框架中。我慶幸自己生長在一個英華並重的家庭,現在我更覺得住在北緯 37 度的平行線上,可以細啜韓文是一種福氣。
上至天文下至地理,不管原著來自任何國家、屬於任何種類,只要是市面上稍有知名度的國際著作,大部份都有韓文譯本。韓國人活在極其單一的語境中,卻可以輕易通過自己最熟悉的文字窺覰四海。
我很希望馬來西亞的出版消費市場可以蓬勃地發展,但主觀一點來說,我們太乏善可陳。全世界有 8 千萬人使用韓文,而包含新加坡、汶萊和印尼在內,使用馬來文的人數也同樣接近 8 千萬,但是我在自己國家的書局內卻很難找到馬來文書籍。
我始終相信一個國家要富強,必須先從振興教育體系做起。而要實踐這一點,從建立貯藏知識的人文寶庫開始。
韓國的書局一般叫「文庫」,不無道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