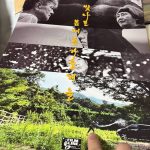我的下屬當中有個性格過份開朗的女生。
平常說話聲調起伏大,對甚麼事情的反應都很鮮明,表情特別豐富。聽到有趣的東西總會冷不防地爆笑,永遠都是嬉皮笑臉的。
光看我的描述,很多人肯定覺得她可能很豁達,形象很討人喜歡。
或許。
人還真的很好,凡事想法都很積極,而且對工作很有熱忱。但其實,我個人很不喜歡她的言談舉止。我也在業務評估當中,很坦白跟她說過。當然,我不喜歡是有理由的,這點我有清楚說明。
因為,我在她身上看到自己。
我知道若干年以前的我像她一樣說話聲量逼人,做事情魯莽粗率。像她一樣走路不看好前面,總會踢到垃圾桶。像她一樣和同事聊天的時候語笑喧嘩,旁若無人。
但韓國 40 歲的大叔都是老成持重的,老小孩並不受歡迎。不,應該說會惹人詬病。我不願一輩子吊兒郎當、輕佻浮薄。所以我很努力地壓抑自己的情緒,讓人覺得我雖然有不懂的東西,但至少思路穩重,可以獲得最起碼的尊重。
我總會招惹很多別人寄予的期望。
因為是馬來西亞在韓僑民協會的會長,我在大使館舉辦的好些活動中必須上台致辭。有過不少舞台經驗的我,還是會害怕。不是因為怯場,而是因為要能說會道,必須確保文思敏捷、言之有理。
如果我現在 20 多歲,是個代理級的員工,我自然可以在客戶提出的問題前面承認自己所知不足,必須請教上司。如果我是 30 多歲的課長,還勉強可以表現誠懇,希望客戶體諒我在成長中付出的努力,但仍然有待改善。而在韓國,當上了 40 多歲的次長,整個社會就理所當然地希望我自己對晉升為部長有所期許。
要回頭去諮詢老闆?客戶立馬判斷我不夠專業,所託非人。因此死活都必須自己撐起整個項目。不懂,也必須表現面面俱到、說話頭頭是道。
我講英語和華語的時候自然流暢,可以武裝自己,別人聽來我是一個有用腦的人。但韓語始終還不屬於我的身體,我無法用這個語言來算數,遇到概念複雜的東西,無法應答如流,別人聽來我成了小學還沒畢業的黃毛小子。
活得像馬來西亞人,我覺得輕鬆愜意。我們是很隨和的民族,不會去計較細節,談得開心最重要。而活得像韓國人,就必須注意外表體面,看身份、看級別、看權勢。
文在寅總統在不久前拜訪馬來西亞的一個聯合記者會上,不止用錯了印尼語的 Selamat Sore 向首相敦馬哈迪問候,還發錯了音。但不以一眚掩大德,馬來西亞的媒體並沒有把這件事情放大來講,鞏固實際的外交關係比較重要。
而韓國就不一樣了。好些主流的媒體抓住這個微過細故不放,大肆批判。外交部長康京和很鄭重地道歉了,我身邊的同事朋友看到新聞也覺得顏面無存,覺得韓國太丟臉了。
據說他們當時找不到人來核實,也不知道有沒有人因此丟了飯碗。
總統,下次打電話問我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