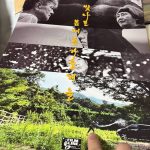我是一個嚮往安定生活的普通人。買房子,肯定是為了住,不是為了投資。
在廈門的時候,可能因為還年輕,沒有想過購置物業。剛到當地的 2003 年,我住的小套房時值人民幣 40 多萬。離開的 2010 年,就翻倍飆升到 90 多萬了。和曾經一齊旅居廈門的幾個檳城人搖首頓足,懊悔當初怎麼沒想到融資買一個單位,只要幾年時間就能賺一筆。
有人說,房價就是城市經營的最好註解。我後來在 2012 年回去探望同事朋友,才不過短短的兩年,就看見鋪天蓋地的變化。廈門更多高樓林立,到處都塞車,和我最早去的時候判若兩個地方。
檳城同樣日新月異,特別是我念念不忘的丹絨武雅。感覺上我們的發展步伐比其它國家緩慢,卻也同樣經歷時過境遷。
在海南村生長的大表哥讀了前一篇文章,感慨自己也要很努力去回想老家原來的模樣,也突然開始緬懷起小時候看到的花晨月夕。
網上看過日本長崎縣島原市的排水溝裡游來游去的錦鯉,很想去看看這幅神奇的畫面。但大表哥一提醒,才記得巴士總站出現前的老屋後面的景象。
那時候家家戶戶的廁所都在室外,有一大片孩童歡蹦亂跳的草地,還種了許多花草樹木。鄉野間萬壑爭流,那個年代的溝渠裡面,有孔雀魚串游。
可是,我很自然地忘了。
從 80 年代末期開始,許多發展商開始對丹絨武雅中,大自然與社區休戚與共的生活模式虎視眈眈。大馬路旁的店鋪夷為平地,要蓋商業大廈。舅父、姨母,還有隔壁的所有鄰居,都被安排搬到拆走菜園、雞寮換來的新木屋。
原居民每天起床就可以看見大海的權利,突然成了奢侈的習慣,此後要從往裡面遷徙的新家走出來。諷刺的是,後來搬進商業大廈的住戶,卻突然被賦予了眺望蔚藍海面的高度。
當時應該沒有幾個人會預測到,這裡的房價也會翻倍。任誰都無法想像,這樣淳樸的一個地方,後來被迫變成今天的高尚住宅區。因為蜂擁而至的村外人,後面的山要削平,開拓成新的住宅區,寸土必用,寸利必得。
而我長大以後,在乎的東西不一樣了,終究也成了默許環境被大肆破壞的共犯之一。每個週末從市區回到丹絨武雅,我開始會嫌棄木屋的廚房髒亂,會嫌棄晚上睡覺蚊子多,會嫌棄下雨天偶爾從屋頂沿著鉛板滲入房內的水滴。
我在珍珠山 (Pearl Hill) 上買了屬於自己的地方。從山腳下的駱葆亨路經過,看著支撐巒環山崖度假屋,感覺上岌岌可危的水泥柱,心想何年何月會像現在拉曼學院附近的住宅一樣,因為山坡被侵蝕而土質鬆動,結果崩塌。
家裡的窗口偶爾會看見生態被邊緣化的鬱烏葉猴 (Dusky Leaf Monkey) 瞪著我看,不知道對人類有多少怨恨。某天晚上回到家,客廳裡闖進了一條水蛇,我卻習以為常地拿了報紙和空盒,開窗把牠扔回大自然去。
恕我無法改變發展,只能學會珍惜和保護當下,不讓它更加惡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