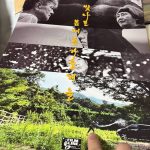大伯父一生未婚,一直和我們住在一齊。爸爸傳承了爺爺的衣缽,經營起咖啡店,沖泡飲料的頭手就是大伯父。這是我懂事以來對這個家庭結構的認知。但奶奶總會有意無意地說起一個送去了香港的「女兒」。
這些顯然都和中國沒有關係,因為這些都應該是移民到了南洋以後才發生的。
但是很多事情只有大人知道,小孩子不能問太多。隔了另一個國家體系,隔了 3000 多公里的千山萬水,隔了半個世紀的滄海桑田,若非這趟尋根之旅,或許再也沒人會提起。
奶奶收在鐵盒裡的信件,其實是兩張分別由兩個不同的署名寫了,一齊送出去的。遠房堂嬸領著我們到了上梨園,找其中一個和奶奶同姓劉的寫信人。
這是一個更小的地方,一群人閒坐在村口一個小廣場上下棋、聊天,幾個小孩在大人的視線範圍內蕩鞦韆、嬉鬧,看見我們幾個打扮和行為怪異的外地人。
「這個劉先生是我父親!」
一個年紀大概四十歲的中年男人,很興奮地帶我們到了家裡。
穿戴著軍人衣帽的劉老先生看了信,激動得像中了樂透頭獎 200 億韓元一樣。老淚縱橫地告訴我們,奶奶是他的親姑姑,比他大幾歲,從小感情非常好。在他十來歲的時候,嫁過去溪東村,然後帶著兩個兒子,坐火船出了南洋,從此沒再見面。
在馬來亞的生活,並沒有如離鄉前設想般順利。一來賺錢的機會多,但是除了要面對一樣從中國過來的基層同胞,也有很多競爭來自於迥乎不同的其他族群;二來,環境和習慣要改變,照顧不好身體就窮病交侵。
我有時候也自己會說「窮就不要生一堆小孩」這種風涼話。但是對於生活困苦的平民來說,好像自古以來都有一種需求,渴望讓孩子成為自己未來可以依靠的親人。
既然明天不一定會更好,而要真正改變現狀,就是不斷尋找和創造可能性。多生一個,雖然可能導致生活更加貧無立錐,但也可能突破人生悶局。
遺憾地,事與願違。
爺爺和奶奶在英屬馬來亞生了第一個女兒。我的爸爸是最後一個孩子,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 1950 年。
奶奶一生中病得最嚴重的一次,走到了鬼門關前,爺爺已經瀕臨絕望,認為生活已經無法繼續,準備好全家在天國再遇,帶著幾個孩子去跳海。
結果,奶奶熬過來了,但二伯父淹死了。為了減輕生活負擔,姑媽被一個同鄉帶去了香港。至於有沒有聯繫,我就不得而知了。只是,我從來都沒有真正聽過他們的事情。
中國開放好些年以後,有人從家鄉去過馬來西亞幾趟,找到過奶奶,親手把信件交給了 1965 年以後開始守寡,依然不識字的她。
我們這才反而從劉老先生,也就是奶奶的侄兒,即我的表伯口中聽到這些長途跋涉回到家鄉的故事,倍感唏噓。
奶奶個性內斂,果然是個飽經風霜卻不露辭色的人。這些年以來,在她高 EQ 掩飾下的內心,能沒有驚濤駭浪嗎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