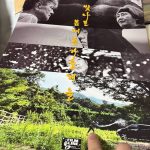我在 1991 年參加小學六年級檢定考試 (UPSR) 的同時,對自己在 2020 的模樣毫無浮想。家人想既然唸了口碑不錯的協和小學,如果考上鍾靈國中,就是雲程發軔的開端,向著的就是一條康莊大道。
我自認從來就不是志堅行苦的好學生。
當時出現了兩套的馬來文試卷,除了原本按華校非母語水準出題的,還有國民小學同等級的版本。要是選擇後者,考了個 A 就可以跳級,上中學後免讀一年預備班。
但要是應付不來,就可能丟了 A 還影響整體成績。我不是學校的第一優秀班,根本沒有飛黃騰達的夢想。所以選擇了普通試卷,做好唸 6 年中學的準備。
公佈成績那天,男生都在看自己是不是去代表檳城文宗學府的鍾靈國中,好像要是去不了就等於下半生的起跑點輸光了,從此不堪造就,命運坎坷多舛。
我順利去了不負眾望的「名校」但成績平庸。保守無過地走完高中,對考大學也沒有多少想法。反正沒有很稀罕本地大學,經濟條件還行就去私人學院唸個好一點的學位,這是當時比較主流的思路。
回想起來,我們的社會還真是從小就在培養勢利眼。整個義務教育制度中,不停以 A 為基準,認定學生的成功主要取決於名校的出身。但我還是比較幸運的,成長的年代和環境並沒有多少兢短爭長的壓迫。
財閥壟斷市場的韓國,是出了名把升學主義和文憑主義發展到極致的社會。每個人一旦踏入中學,就要開始邁向大學奔跑起來。
幾乎大家的目標都是一致的,要擠進薪水優渥的大企業,就要先擠進頂尖拔萃的大學。而要進入大學,就必須先通過大學修學能力考試,簡稱「修能」。
這是相等於馬來西亞教育文憑 (SPM) 的全國學業水準測試,對於韓國學生考取大學至為關鍵。而且,這是克服高中生涯裡艱辛溫習的日子後,用一天時間去參加的評估。
由韓文、數學、英文、歷史、探求(社會、科學、職業)、第二外文或漢文等六大部份組成,考生從早晨 8 點 10 分進入考場後,一直到下午 5 點 40 分,必須在九個多小時內完成所有考卷。
下午 1 點 10 分至 35 分進行的英語聽力測試,更可能是韓國一年之內最寧靜的 25 分鐘。因為要避免造成聲浪而影響應考生,全國還暫停飛機升降、火車班次。
上司崔先生的長女今年赴考,前一天就提早下班回家打氣陪伴,確保孩子適當放鬆心情,睡眠充足。第二天,實施交通管制,確保受驗生有道路優先使用權,甚至勞師動眾警察去協助偏遠地區的孩子準時抵達考場。
我有買股票,當天發現過了上午 9 點都沒開市,才驚覺所有銀行和證券所都會延遲到 10 點才上班,大部份企業也會讓員工 10 點出勤,以免影響交通。
不少家長會在寺廟、教會等地方集體禱告,大家都把這個考試當作自己的事情一樣。抗疫的過程中,抱病或接受隔離的學生有政府做特殊安排,保障每個應考生的權益。
理性地分析,我覺得這種一試定終生的怪象不見得健康,更顯示價值觀和社會結構的失衡。但韓國人普遍認為萬般皆下品,唯有讀書高。一個國家有多發達,有時可以看這個國家有多注重教育和社會發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