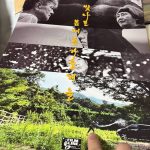韓國的社會建立在一個不斷分朋樹黨、拉幫結派的基礎上。公司、學校、社區各層面的人幾乎都無時無刻要小心拿捏自己與別人的關係,相互間的稱謂常顯得無比重要。
我在工作上和客戶通電話,必須先搞清楚對方的職級。我之前有說過,有時忘了對方的姓名還無所謂,記得職級就能忽悠過去,不會得罪人。可是勤務以外的時間,要是關係好到會出來喝酒吃飯唱歌,按彼此的實際年齡稱兄道弟的,還算挺常見。
韓國人特別注重「三緣」。這應該跟儒家倫理的社會秩序觀有關。
許多人到今天依然非常在意「血緣」的親疏,就連我在高科技的工作環境中也能深刻感受到。我在檳城一個唐人文化非常濃厚的氛圍中成長,很自然能理解這種對血緣關係的依託。
遇到同一個姓氏或籍貫的人,感覺特別親近。就算同祖同宗沒有特別開心,也可能會在某個聊天的點上偶然提及。
美術部一個姓盧的同事離職,總裁盧先生居然約他和我們幾個平時玩得比較近的,出去大吃一頓餞別。兩人姓盧,說不定上古一家親還無所謂,燒烤桌上除了我以外,居然大家都很巧合來自比鄰首爾的城南市,都是有「地緣」關係的同鄉。聊到家附近有哪些地標哪段回憶的話題,我只有想像的份。
還好,沒人來自同一所高中或大學。否則「學緣」把幾個同校的人湊在一齊,頓時成了學兄學弟,彼此間打開更多話匣子,我就真的完全是局外人了。
其實回頭想想,我們在馬來西亞不也是同樣有類似攀親結義的時候嗎?混得熟絡的,我們也會阿春姨、阿山哥、阿蓮姐這樣叫,大家都是自己人。甚至稱呼資深國會成員林吉祥先生為 Uncle Lim 的不在少數,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茲莎還是 Kak Wan 呢。
雖然民間偶爾這樣叫可以製造親暱互動,但所有公開場合都這樣浮浪不經就可能有失大雅了。
大使館都會有三個秘書,當然駐韓馬來西亞的也不例外。一等、二等、三等秘書實際上並非等級的高低,而是按工作需求和個人能力來分配。
在首爾的三等秘書是個年紀比較輕的男生,外交資歷相對淺,但是和留學生混得很熟。所以在自我介紹的時候,讓晚輩們叫他 Abang Fandi 就好。
副首相微服出巡首爾的那次飯桌上,就有留學生很不經意地這樣叫了一聲。大使皺了一下眉,很溫和地指點了一下。
畢竟這是一個接待我國高官的正式場合,大家理應處於工作的狀態,就算彼此私底下是不拘形跡的爾汝之交,在這裡都必須知分寸、識大體。
像朴大哥,他在職場上是任員 (Executive) 之一的「常務理事」,屬於高級管理職級。要是有一天我在某個工作場合上和他打交道,肯定要在眾人面前稱呼他「朴常務」,絶不能兒戲。
但是週末出來吃飯喝酒看世界盃,他還是我的朴大哥。